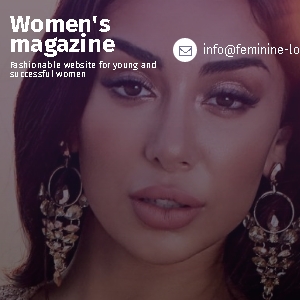當我在以前的博客中寫道時,嬰兒的誕生讓我進入了一個副業。加入這個大腦進入脯氨酸,一般來說,繪畫一張照片。但我有義務,因此,出生後三週,我出現在辦公室。我想說我,盛開的,不是很年輕的母親被截斷到辦公室的員工的喜悅,但沒有,一個厚厚的醜陋的幽靈來到辦公室,瘋狂地想睡覺,搞砸了他的肚子,是否返回了。她沒有回來,那些不知道我會生出來的人,問我是一個快樂的事件,而不是在沮喪中掙扎著。但生命正在沸騰,工作繼續。只是該頻道改變了第一次會議後的所有者我意識到我不工作,但我們正在為時尚人士獎項獎項獎項獎項獎項,我有義務提出贊助商,我告知新的指南我在留下的新指南保費,並陷入準備。領導力並不相信我,我再次消失了辦公室的日子和夜晚。塞雷達,消失了多天,晚上穿著孤立於手中的戀人尖叫的菲普斯坦人,他的肚子受傷,它根本沒有睡在他的手柄上,然後出現了一些嬰兒問題。而且儘管我們有一個保姆。前三個月的孩子根本沒有睡覺,只在他手上,它來自我的經驗,因為我以為我的母親。我一直很自豪,我的兒子從床上的第一天睡覺,從來沒有必要把他下載到他的懷抱中或每晚起床10次。我向女朋友分發了建議,如何教孩子自己睡覺,我寫下了我的頭,學習另一個媽媽投降並把孩子放在床邊,讓自己落在床邊,因此它結果絕對不是準備好成為我自己的寶寶將成為那些分享所有理論的孩子關於如何在絨毛和塵埃中撫養孩子。
從晚上八點開始,他開始哭泣,我們在懷裡戴著它,所以他被解僱並忘記了一個不安的睡眠。值得把它置於或至少只是坐下,他先立即睜開眼睛,然後是一個大粉紅色的嘴巴,並出版了這麼長的“a”,使命立即開玩笑,再次開始在房間裡徘徊。一個月後,亞利桑那州或華盛頓發現緊急事情,他擔心留下了一周,因為我懷疑,只是睡覺。我們一起住了一個保姆,菲利普和她一起喊道:晚上上半年 - 在我身上,第二 - 在她身上。經過一段時間,我放棄了,他緊緊地在我的床上沉默,只要我睡覺,我只睡覺,只醒來食物。我不知道如何避免這種情況,但他已經在那裡解決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他四年,它不可能識別它。很長一段時間,他在晚上吃了,然後喝了,然後是一個新的樂趣,然後是夜晚的問題的形式“媽媽,你在這裡,你在做什麼?”或者“媽媽,吻我”。在4歲時,丈夫堅決解鎖他。不,不是在一個單獨的房間裡,但至少在一個單獨的床上。正如它所發生的事情 - 一個單獨的話題,我肯定會講述它,我自己的瀏覽中的最終停藥發生在一個可愛的菲利普斯 - 亞歷山大,只在6年半。在這裡,我可能會說“不要重複我的錯誤”,但是,如果老實說,我不會是一個心靈,就像你避免它一樣,因為“離開孩子喊道”不是我的選擇。
好吧,我再次工作我的母親:在晚上回家,我聽了“今天的菲利普就學會了,”今天轉過來“,”哦,他學會了崛起的手柄。“與長子,我沒有選擇“不起作用”或至少去法令,兒子的誕生恰逢離婚,所以有必要生存,但在菲利普的情況下,一切都不同。我明白我不會讓我去任何法令,每天我都更強大,決定在獎勵之後是唯一的真實之一。
然後來了4月。正如所有記者都寫的那樣,這肯定是當年最生動的事件,也許是整個職業生涯。我仍然為我的團隊感到驕傲,也為這項工作感到驕傲。那天晚上,非常複雜的感情是在我身上的,我明白這是我所做的最好的事情,但這是最後一個。一種感覺非常感覺。我對右邊笑了笑,留在相機上,看著所有的明星,記者和朋友,思考他們在明天來看有多少人會從我的生活中消失。我只對我的團隊決定了。向前跑來會說至少我已經準備好了,我的手機越來越少的來電,但我肯定還沒有為他幾乎不再呼叫而準備好了。在我傷害著盔甲的多年的工作中也是好的,我基本上構成了一些傷害,幾乎不可能冒犯。我被我對朋友類別的人失踪了。我期待來自Celabritis和記者,因為那裡沒有友誼,我們需要彼此,但在你的朋友們下令人沮喪是驚人的。但我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意識到了我所做的那麼多,因為我與許多記者,攝影師和世俗生活代表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但良好的關係和密切友誼仍然不一樣。但那天晚上,我還不知道這個,剛剛享受了最後一天的工作。
第二天,我帶來了關於護理的陳述。領導沒有相信,決定我是一公公幾,但我想過我的生活。成為一個媽媽,了解我的孩子如何增長,而不是讓世界上最好的保姆,但最多的人。我如此錯過了他小生活的四個月,所以我堅定地決定了幾年我有權嘗試只是我的妻子和母親。
我們沒有對另一個國家的全球決定。我們決定夏天將花在羅德斯上,然後決定去哪裡。因此,沒有思考而沒有思考,收集兒童和包裝手提箱,我們就像徒遊的鳥類一樣,伸展南方。很難說,我現在會再做一次,因為那時我不知道我從莫斯科離開了什麼,如果不是永遠,那麼很長。我從來沒有後悔離開工作,不喜歡移動,這可能是不值得的,這麼敏感我的生活變化。我從我自己的前生命和真正的朋友,通常的錯誤和其他事情中醒來。起初很好。就像你來度假村一樣,一切都喜歡:藍天,海,鮮花和粗心。然後,當你遇到另一種文化時不再是旅遊者,而是作為一個必須接受它並成為它的一部分的人,那麼困難就開始了。
希臘,我總是愛我,直到現在,但在我們的舉動之前,我無法留在島上超過2週的島嶼,所以弱勢想像了等待我的事情。我正在等待許多驚喜。漸漸地,我學會了當地的習俗,其中許多人都驚訝了我,有些令人愉快,甚至生氣。好吧,例如,希臘人的永恆慾望觸及孩子,從邪惡的眼睛轉向他。菲利普每次從嬰兒車搶走他時都會哭泣。 “在一個人,一個男孩被撫弄著,”我丈夫的熟悉的父母搖擺。 Yani的父母自己是非常進步的人,他們在美國生活了大部分生活,所以他們只笑了,看著我的驚訝的臉。但是,當我被告知你需要清理那些試圖偷走靈魂的惡魔中,只有一次,我只遭受了一次淨化程序已經開始,一些老年女性進入黑色長袍,開始受洗,在菲利普的一側翻轉,並試圖在她的懷裡抓住他。我坐在嬰兒床和他們之間的牆上,他從黑人陌生人的豐富哭泣哭泣,他們很感到很感到注意到一切都應該因為它而不是哭泣,而且他正在哭泣,因為惡魔會去的事實他最後。我說,如果現在這個Vakhanalia沒有停下來,我飛往莫斯科第一飛行,我叫Jani,誰在商務旅行,並沉默寡言。 yani徘徊在電話裡說不要注意。老年女性,一切都令人失望的是,當我提供披薩和一些茶時,他們迅速安慰。對於茶,決定沒有惡魔不是,只是在男孩中,牙齒被切割,牙齦應該潤滑給他。 uzo是一種隨著ANISA的增加的Moonshine的格拉帕。只有我平靜下來,所以再次緊張,當我拒絕時,菲利普很快塗上了Uzny的牙齦,它肯定會影響他未來的生活。在希臘,順便說一下,通常就像孩子和舒緩一樣,它們都是麵包,略微濕潤在uzo或牙齦。我的意思是希臘,在首都,當然,偏見少。支持這一點,孩子們不斷努力嘗試口中的任何食物來自穆斯卡卡到甜蜜的Bakhlava的食物,考慮到他仍然在混合物中,只開始通過我的愚蠢地以夏南瓜形式接觸。偏見,你會明白我不斷守衛,只是沒有時間思考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