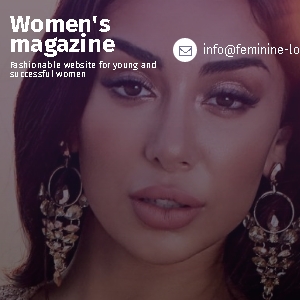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一个惊人的女演员,一个强大的人...... arrowsee立即贿赂她的仁慈,幽默和一个有趣的警告:“我有恐惧我,我可以说尖锐,准备好。”与此同时,她非常好,迷人,她的故事着迷。
我们很久以前准备了这次采访,并计划在12月份发布它,特别是对于Olga Aleksandrovna的生日。有一段时间过去了,我们在电影院遇到了她,我内疚说,材料尚未出来,并听到回应:“没有什么可怕的。将会被释放。如果你忘了稍后给出的实例,无论是什么都不糟糕。我更喜欢书籍阅读,而不是关于女演员Olga Arospea的任何东西。“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经常没有时间说一个好人,这一切都很棒。我们都记得你,Olga Aleksandrovna,让这种材料成为你的记忆致敬......
Olga Aroseva:“我的母亲,Olga Vyacheslavovna,毕业于贵族贵族研究所,但时代已经改变了 - 她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我爸爸亚历山大·雅科夫豪光,是他参观了监狱的皇室时间和链接中的着名Bolsheviks之一。参加了1917年的革命。在苏联力量的第一年开始,开始从事文化和外交活动。因此,我童年的一部分通过国外。我们住在瑞典,然后在布拉格。我的父母离婚了。和三个孩子 - 我和姐妹 - 住在父亲身边。“
作为一项规则的离婚,前面是争吵和丑闻。
奥尔加:“没有这样的家庭。爸爸是一个相当克制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母亲,很少拒绝她。例如,当我出生时,我父亲们又禁止芭芭拉,得到了一个公制。经过三天之后,妈妈了解到它和愤慨 - 她不喜欢这样的名字。然后他们决定我会打电话给Olga,并转换文件。事实证明,我在烹饪中度过了第一天,而Olya以后变得越来越多。 (笑。)我不记得父母之间的冲突。只是他们分手了。妈妈有一个新的家庭。我不带她去谴责她,特别是因为时间已经表明,它为我们而言,孩子们更好。“

Olga Aroshev在电影节开幕“微笑,俄罗斯!”。照片:Fotodom.ru。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发现自己在剧院?
奥尔加:“当我的父亲和我的姐姐,娜塔莎和莉娜带到维也纳歌剧院时,我已经五岁了。从捷克共和国,我们在那里生活,你可以乘车到奥地利的首都。这次访问我记得直到现在:和奇观本身,演员和风景,以及视觉厅的美丽装饰,以及我们有地方的小屋。真实,姐妹笑,笑,说我无法在我的记忆中拯救那一天,我熟悉他们的故事。喜欢,我太小了。但我相信我依靠我的个人记忆,甚至在我看来,我觉得自己的香水的味道是那些来到性能的女士......“
之后,你决定成为一名女演员吗?
奥尔加:“不。我经历过的喜悦,首先在剧院时,自然是任何有灵魂的普通人。在女演员,我在布拉格拉我,我看着“三烟囱歌剧”Bertold Brecht。在没有推迟实验后,我的女朋友和我第二天剪了我们的衣服,染了它们(因为服装会被告知 - Zafakturili)就像在比赛中的英雄一样,并且这样的形式去了街道。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关于不幸的艰苦生活和施舍的含泪故事。正因为如此,丑闻几乎爆发了:如何如此,苏联外交官的女儿在捷克街道繁殖!当然,爸爸并不了解这是我的滑稽动作。但我没有停止表演,相反,我鼓励我提供了它看起来不同。所以我开始在大使馆的晚上表演。甚至在德语咏叹调中唱歌,艾利亚·波希。“
你什么时候回到莫斯科的?
奥尔加:“1933年。爸爸成为全联博物会文化关系协会主席。我们在全国“堤防上的房子”中定居。我们的公寓里只有什么名人没有发生过!和Henri Barbus和Boris Livanov和Georgy Dimitrov,而罗曼劳伦斯甚至与我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祖国善待你?
奥尔加:“你可以这么说。虽然时代仍然不安。产品被释放到极限。我记得是因为我没有强大的健康,医生推荐我吃更多的石油。在晚餐时,我总是给了一件额外的一件,我涂上了面包,把它带到了我没有人看过的房间里,在外面的窗台上扔出窗口。当父亲找到它时,他抓住了我的领子:“你在做什么?!在这个国家,卡片,它使窗台用油!“尽管如此,我很高兴。这么多精彩的人被我所包围,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一旦我,我也把我的妹妹带到了塔伊诺的航空游行。有很多熟悉的父亲。 ChileVoroshilov和Lazar Kaganovich。但是,我对起飞领域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但人们的背部位于我们面前。突然间,我听到了强调的声音:“成年人起床,让孩子们不可见?”斯大林走近我们:“谁是?女儿arossev?“他带着他的妹妹抱着我们的妹手,带领第一排,和我们谈过,转向“你”。问:“你多大了?”我回答:“二十头12月将是十分”。约瑟夫visarionovich给了我一束鲜花,笑着说:“然后让我们一起庆祝生日。”

她有一个很好的幽默感。因此,也许方向经常提供她喜剧图像(来自电影“Trebita”的帧)。照片:Fotodom.ru。
假期如何指出 - 在一起?
奥尔加:“当然没有。但是我今天去了克里姆林宫,为他带着鲜花。冬天,寒冷......所以绣球花僵硬,我把它包裹成一捆。当保安没有让我走到并开始粗暴包装时,我问:“有鲜花,他们会在寒冷中死去。”其中一名军官命令我等待,拿走了我的礼物,进入了守护室,然后没有一束返回。说:“斯大林同志非常感谢你祝贺你。但是,不幸的是,他现在正在从事国家重要性,并且无法与您沟通。“现在我明白我的祝贺物质并没有到达他一样,而且鲜花最有可能留在警卫中,然后我真诚地相信我告诉我一个严厉的军事。重点不是我幼稚的愚蠢,几乎整个国家然后留在天真的兴奋中。甚至逮捕父亲并没有把我拉出来。虽然,如果你想到的话,令人震惊的钟声已经响起。“
哪一种?清洁你爸爸的朋友?
奥尔加:“不。孩子们不付出这种注意。另外,我们试图隐藏正在发生的事情。另一件事是同龄人......我的姐妹和我在德国学校的Kropotkinskaya学习,学生中间有突出的各方,高级官员和外国共产党人。来自同学的人突然停止了上课,有人进入了泪水,他在他的背后低声低声说,他的父母在晚上被拍了......但是,我承认,我没有赐予它很重要。似乎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不是与你同在。在1937年,他们逮捕了爸爸。我充满信心 - 这是一个错误,否则你不能。我会弄明白并放手。等待。而且,正如你所理解的那样,徒劳无功。在这里真的值得记住我在我们的谈话开始时所说的:父母的离婚结果表明是一个祝福。毕竟,如果其中一个配偶进入磨石的时候,那么同样的命运最常威胁第二。但是,妈妈长期以来一直与另一个人结婚,她没有触及并允许她给她女儿。所以我们避免了孤儿院。“
失去父亲的犯下?
奥尔加:“我写信给斯大林的信,相信他将在一个怪物错误中弄清楚,NKVD制造。在家里打算我,他们说你需要获得耐心。同时,句子将是:“没有通信权的参考”。那时我没有猜到它意味着射击。我们认为爸爸活着,他在营地的某个地方,当一切变得更加清晰时,他会回家。毕竟,他没有犯任何内容。当我的姐姐娜塔莎·娜塔莎队已经是一名Komsomolic,被放弃的父亲时,更强大的是我的震惊。了解它,我用拳头踢了她,我打败了她,她甚至没有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她被迫这一点,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这种硬的压力,甚至更多所以一个女学生。这种行为从内部啃了它,自然地,她很担心,无法原谅他的一生。当两年后,轮到我来加入VLKSM,他们也被迫拒绝爸爸,我没有这样做。因此,Komsomol没有组成。而且我并不后悔。虽然我马上说,但不是我比姐姐更强壮,我不能打破。毕竟,时间已经通过了自判刑以来,虽然我把一个标签的“女儿的敌人的人民”,但他们仍然没有像纳塔利娅这样的陌生人。虽然,潮湿的追求更残忍,她不得不比我更难。而在中期,我了解到,当时所有这些戏剧性的事件都展开,父亲不再活着。逮捕后不久就被枪杀了。“

自1950年以来,Olga Aroseva于自1950年以来在Satira剧院工作。照片:Satira剧院。
你还记得战争是如何开始的?
奥尔加:“当然,我十五岁。不要忘记令人震惊的面孔,那些聚集在街道上的人群,令人惊讶地令人恐惧地沉默地听着收音机。然后没有人知道战争会持续多大。不相信,但起初有信心不久,我们将轻松地击败所有的敌人。但是,唉,每天都在我们身上的麻烦规模,迫使一切更清晰,更清楚。我记得第一个开始做邻居的葬礼。这种痛苦与他们分享了整个房子。还有人报告说,你个人的个人不再是。我读了很多书,看过最近关于我们生命周期发布的电影,我看到了一些坚实的Chernukha。喜欢,几乎所有的圈子都是叛徒和恐慌,每个人都为自己。但是这是错误的。当然,不同的角色遇到了,但是现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待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普遍的整体悲伤,许多人已经为他们的人民抢了一些事情。我的妹妹娜塔莎留下了志愿者到了前面。幸运的是,她从活着的战争中回来了。莉娜比我年长两年,去上班工作 - 建立防守的设防,我被问到她,我被允许,尽管我的年龄。“
你为什么不离开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奥尔加:“当我和我回到工作岗位下班时,我的母亲已经疏散了。她离开了打算跟随她。但我们认为并留下来。一般来说,我想分开地说Lenochka。我们始终与她完全密切相关。重点不是我们对年龄略有差异。这不仅仅是爱情,而是灵魂的一些特殊统一,即使在远处也会感受到。血统关系和家庭团结都没有保证他们与SIS联系的这种关系。即使是对剧院的爱,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如果您知道我们必须为门票捍卫队列的次数!毕竟,在我们年轻时的时代,他们并不那么容易。我们接受了在一起留在首都的决定。 Elena进入了剧院学校。我也想要,但我没有收到完成的十级课程证书。没有它没有。但在马戏团拍摄。自马戏团是我的第二个,在剧院之后,激情,我决定去那里。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半,同时接受中学教育,然后成为莫斯科市剧院学校的学生。是的,我从未毕业过他。“

Olga Aroseva很高兴亚历山大Shirvindt指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讽刺剧院。 “Shirvindt不会破坏,骨头会落下,但他不会给另一个人,”女演员肯定。照片:Satira剧院。
但是你是如何在列宁格勒喜剧剧院发现自己的,你在哪里开始职业生涯?
奥尔加:“这是一个显着的故事。然后我在歌剧院的剧院工作,帮助装饰者。这时,Comedy Nikolai Pavlovich Akimov的列宁格勒剧院的剧团被莫斯科从疏散撤退了。顺便说一下,他们不是缝隙的人,而是最着名的剧作家Evgeny Schwartz。然后刚刚通过他的戏剧“龙”演奏了第一个表演。我记得,我从Papier Masha,Stones做了一些树木......和某种方式,Nikolai Pavlovich,注意到我,问:“你该怎么办?”我回答:他们说,树是Poupe,但一般来说,我是未来的女演员,完成剧院学院。他建议:“如何走出去,来到列宁格勒。我们需要年轻的才华。“而且我受到这种建议的启发,坐了一个姐姐的文凭,并前往涅瓦河上的城市。他们听着我,一切都很棒。但是在第一次上有文件存在问题。在文凭上,旁边的姓arosov,e的首字母。我开始撰写我的名字是奥尔加,但每个人都称之为莱利亚,因此这个错误。大学的政府决定我是艾琳娜,所以在论文中并记录。简而言之,我带着一些废话,在我看来,我躺在我躺着,尴尬是明显的。但在剧团中,我还在注册。在同一个地方,在列宁格勒,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个丈夫。他不是演员,而是一个创造性的人,一个有才华的音乐家。我疯狂地爱上了他,尽管年龄差异是必需品 - 十年......但是在1950年,我们分手了,我回到了莫斯科。“
在你这么努力终止婚姻,你决定移动了什么?
奥尔加:“绝不是......在这里,我的生活中有一个不同的事件。 Nikolai Pavlovich Akimov的伤害开始,举行会议,他的“颠覆性活动”被谴责,他们开始转移。我不能参加这一点。而不是因为我很棒和好。相信我,关于我的角色说,这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仍然添加“婊子”这个词。 (笑。)但我不接受背叛。我自己不能这样做,我不可胜地很难看待别人如何进入这一步骤。虽然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甚至可能不是一个养育的问题。它就像一种血型。如果你出生在第一个,那么你永远不会有第四个。因此,我决定向列宁格勒喜剧剧院和1950年以来向讽刺剧院发放。 (真实的,三年我有机会在一个小盔甲上玩剧院的场景,但我仍然花了我的大部分生活与讽刺。)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第二个丈夫,演员Yuri Khlopitsky。我们很快结婚......在这个婚姻中,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孩子出生。你知道,以某种方式阅读一版,奥尔加没有孩子,因为她选择了职业生涯。这不是真的!在我的生命中,另一个与斯大林的名字相关的悲剧。我怀孕了,我的丈夫和我在等待宝宝的诞生。突然 - 关于人民父亲死亡的信息。尽管我爸爸发生了什么,但我确信约瑟夫·维多利奥诺维奇与此无关。这是他的周围环境,他自己把人们命令到死亡和阵营。在我的记忆中,他仍然很好,周到,成人的叔叔,因为我在塔伊诺的机场看到了他。因此,我不能去他再见。如果你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疯狂的粉碎,我陷入了她。当然,很大。幸运的是,他还活着,他们是死者,他们分布的,在文字意义上灭绝了。人群实际上是为了他们!但我失去了我的孩子,医生的判决是可怕的:“你永远不会再有孩子了。”因此,当报纸遇到虚拟炒作时,你感到痛苦。最重要的是,你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不得不写这样的原因。因此,我问你,一个可爱的女孩......你不能被冒犯我转向你。我在他面前看到一个年轻女子,谁有很多事情前进,但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岁月和日常生活你还有一个女孩......我真的问你,小心言语。他们可以杀死更快的刀片和子弹。这不仅适用于印刷的单词,也适用于您告诉人们 - 熟悉的,不熟悉的。留出你的讲话,可以覆盖,但可以摧毁。我希望你的读者思考它。“

在电影“干预”的集合中,艺术家遇到了Vladimir Vysotsky。他不止一次在VNUKOVO的达雅地区访问她。照片:Fotodom.ru。
你结婚了四次。第三个丈夫是歌手Arkady Pogodin,第四个 - 弗拉基米尔索拉斯基,他爱上了他的时间。为什么不是家庭幸福?
奥尔加:“你已经制定了我立即记住的问题”普通奇迹“尤金Lvovich Schwartz:”糟糕的事情是结婚了十八次,不计算肺爱好。“ (笑。)是的,我正式结婚四次,还有内情婚姻,而且小说没有最终......我不会谈论我们的男人,就像要叫名字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十字架,他们自己的故事。在我们的关系中,一切都是:和幸福的一段时间,寂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想谴责包括自己的人。真的,如果在男女联盟不去某事,没有一只手,这将是对此负责的。谁是对的,谁不是,不可能理解。就像发生一样,有必要把它作为给定,不要寻找内疚,但进一步努力,不受冒犯的灵魂。“
你说你有一个沉重的,甚至是婊子的性格。改变它没有尝试?
olga:“等等。我说有些人认为我有这样的脾气。我没有说我同意这种看法。然而,我个人适合我,就像那些接近我的人,以及我在毁灭灵魂的人的人,而不是需要。我想给出建议:记住,别人的意见不是行动指南,值得倾听,但他并不总是需要遵循。“
当他们的一个图像粘在一起时,许多演员都被冒犯了。你如何从“十三椅子夏南”提到Pani Monica的作出反应?
奥尔加:“我真的不知道,意外或故意,但你再次强迫我做出异常。当我记得这个女主角时,我很高兴。我很满意。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波兰帕尼记得和爱。莫妮卡 - 骨头的妇女。在一些该死的中,它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例如,她还可以支持关于政治或技术进步的对话,尽管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在这里,我认为它与在贵族少女研究所接受的教育工作。 (笑了
它现在已被告知,电视节目很长一段时间。你没有厌倦彼此?在集合上统治了哪些关系?
奥尔加:“很棒。特别是因为大多数艺术家在“Zabachka”中曾在讽刺剧院服役。我们不仅仅是熟悉,我们之间存在友好的关系,我们会尽可能地互相支持。相反,这套的工作只提供了乐趣。不,我们发挥了我们的角色,但感觉同志在某种派分中聚集在一起。气氛是无歪歪扭扭的,我甚至会说回家。“
他们传闻甚至是Leonid Brezhnev观看了这个程序,他最喜欢的是莫妮卡的锅......
奥尔加:“我觉得我很难回答。我猜这些面包有来自的地方。在其中一个剧集中,我根本无法播放,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想象一下,莱昂妮伊利奇看了转移,召唤谢尔盖·兰那的苏联主席到他自己,他是预先的,为什么他做了原因这次没有看到Monica的Pani。“随着一个严肃的官员,拉普在下面的问题降低了:“aroseva在哪里?不允许将来缺乏这个计划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知何故特别是由当局或人的人统治。永远不要努力。“

与Mkhat的艺术总监。 Chekhov Oleg Tobakov。照片:Fotodom.ru。
您如何看待亚历山大·谢范达以及他领导萨特拉剧院的事实?
奥尔加:“我很高兴是一个男人在剧团的头上起身,我们的剧院意味着很多。这是他的本土fenats,就像我一样。这很棒,因为它往往是远离团队的铰接式的人,这既不是这个剧院的历史,也不是这种场景本身,也没有人们发挥任何作用。亚历山大才华横溢,聪明,他有一个抓地力和组织能力。没有人会更好地保护他,这是重要的,不会增加我们剧院的行李。你知道,因为它发生了:我来自一方 - 即使我是非常有名的 - 一个男人,摧毁了他面前的创造,并没有盲目地(特别用这个词。你可以创造,但有可能塑造如何一段时间从Papier-Masha的树木。 Shirvindt和他自己不会破坏,骨头会落下,但另一个不会给予。并为他留下武力之神,留下来持有这个前哨。“
我记得,有一天你打电话给“带狗的女士”,而且同时你有一只巨大的狗。你如何设法应对这么大动物?
奥尔加:“唉,你说的莱昂伯格帕特里克不再活着。但我不断记住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的品种,但他非常聪明,顺从,我甚至都会说关怀。人们经常低估动物,与此同时,他们有时比其他人更敏感和小心。我有时候会听到:“你和他说什么,好像他是一个男人?有必要命令,因为他们只在反射水平处了解一切。“废话。谁想到了,最重要的是 - 已被证明?!我会举个例子。一旦帕特里克吞噬了我的不小心吞噬了。你甚至没有想象我是害怕的。毕竟,石头或金是城堡,急性结局的地方 - 可能会伤害他的胃。兽医说有必要观察宠物的行为。如果他迟钝,拒绝饭菜,然后立即去诊所。我整天都很紧张。在晚上,我们和他一起走路,他潜入灌木丛中,然后他会逃离那里,跟他打电话。我想:还有什么可能发生的?它爬进了这些灌木丛中,他是一个枪口,对不起表达,表明他的束。我第一次不明白狗的意思是,我说:“做得好的男孩,走了。”他不会消失,仍然击败爪子。突然间,我明白:狗屎是我的耳环。他给了理解:“不要抽搐,一切都很好!健康,吃,代表剩下的危险!“(笑。)所以我不相信反应,但我相信理解和爱情。”
我们谈到了你的姐妹。他们的命运怎么样?
奥尔加:“最古老的,娜塔莎,成为翻译,非常闻名于他的专业界。她写了一本关于父亲的书。唉,它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很长时间。和Lenochka,正如你已经理解的女演员,她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剧院中演奏。她是俄罗斯的应得的艺术家。在她的家庭生活中,她,感谢上帝,一切都很好。我有很多侄子,他取代了我的原生孩子。所以我永远不会独自一人。绝不。我有亲戚,朋友,邻近莫斯科VNUKOVO的邻居,他们成为相关的灵魂,是Leia Ahacedzhakova和Allochka Budnitskaya。感谢上帝,活着,我的妹妹莉娜,我没有茶的灵魂......但同时,寂寞的感觉,正在遇到每个人,独自留在自己的“我”。我不后悔任何事情,我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所以这一切都吓到了我。充满爱情,参考过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淹死。只是生活。而且我不怕任何事情。我的一个基金发出了一个副本,我可以归于自己:“我不怕死,因为我的灵魂是永恒的。”而且上帝,伊莱,命运是准备的,非常有尊严,拥有自己的性格,最重要的是 - 在良心上。我并不是九十年来,以点燃 - 第一埃琳娜,然后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