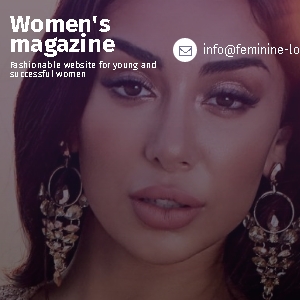Agrippina Steklov和Vladimir Bolsharov近二十年。和Sachirikon劇院的相同數量服務,當Agrippina來到傾聽時遇到的那裡,弗拉基米爾專注於Cudskore。在約會邊緣時,兒子已經給出了,而Volodya - 瑪麗亞的女兒。他們一起成長,互相考慮,最親密的人。並且職業被選中了。 Danila在MHT中服務。 Chekhov在電影院拍攝,Masha最近成為劇院“彼得福梅科”的女演員。
- 盛大,Volododa,它在我看來,不久前,你再次開始了新婚夫婦。我的意思是讓孩子的斷開。弗拉基米爾:我不知道阿格里帕納是否會同意我的意見,但我會說這段時間沒有停止。孩子們干擾了浪漫關係嗎?
阿格里帕納:當然,浪漫總是存在,但直接為自己的時間就是更多。至少是因為孩子不是所有的時間。但它們不斷接觸。特別是如果他們有問題,他們立即繪製,有時甚至會才能與我們一起生存。我們對他們感到強大的依戀,他們是我們的情感短缺。
- 他們為什麼決定單獨生活?
弗拉基米爾:他們開始賺錢,感受到自己的獨立性,決定強調它。
阿格里帕納:這是他們的方式。而且我認為這是對的。成年兒童應單獨生活。他們滿意,我們也是。當然,他們的搬遷是一個嚴肅的一步,因為學會居住 - 一點科學。 Danili一切都恰逢研究所的盡頭,並隨著衛星的出發。他在各種各樣的意義上說:“我想離開家。”走出舒適區。
弗拉基米爾:我們有面孔的安裝 - 不要干擾孩子的生活。當他們來到大學時,當他們學習時,我們才仔細地參加了這個過程,只能在蘇聯水平。對他們沒有壓力沒有。當司那說他不想留在Satirikon時,因為我們在這里工作,它似乎在翼下,不想看起來像一個媽媽金子,“我理解它。
阿格里帕納:我不同意沃體表。司那願意在另一個領土上與我們合作。只是“Satirikon”也是他的房子,他覺得自己的孩子,從這里四年來,他在這裡一切順利。他幾乎立即離開了兩個家園。他相信即使是羅密歐的作用也很容易給他,他想要一個更艱難的道路。

在藝術之家繪畫“Clarch”女演員扮演老師的妻子
照片:Agrippina Glass和Vladimir Bolshaya的個人檔案館
- 圈,不是因為你也積極工作了? “Tartuf”在一個小盔甲上,在Yermolova的“哈姆雷特”,10月在國家劇院的總理......這不是一個完整的清單。
阿格里帕納:是的,可能是,我也有趣的是部分剝奪自己的舒適和寧靜。 (微笑。)隨著他家鄉的所有愛,它餵我,可以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在別人的空間中使用絕對不同的董事和新合作夥伴。這很有用。我很高興我被邀請了。現在在國家劇院排練,如果沒有夢想,我真的想在那裡試試自己。我非常尊重藝術主任Evgeny Mironov,劇院本身長期以來引起了很多好奇心。我在一個相當名的波蘭劇作家Gumbrovich的美麗戲劇中提供了一個壯觀的角色。我第一次與外國導演合作 - Gushege亞澤利。這是一種新的困難經驗,需要額外的努力。
- 孩子們看起來像你的表現形式?
阿格里帕納:在我看來,他們都與我們非常相似。已經眾所周知的人,可以比較事實,了解Danila不能成為Volodya的生物兒子,他們仍然去死胡同。例如,MHT談到了Danya:“他像Volododa一樣談論,像他一樣笑著,開玩笑。”至於我,兒子是我的演員副本,它是我們的品種,在我的祖父。 Masha類似於Volododa。
弗拉基米爾:是的我同意。最近有一個案例,一個女兒開玩笑 - 在我看來,不成功。我把她扔出了,扔了電話。經過時間,我平靜下來。 Mashka說:“爸爸,我不明白,但你在冒犯了什麼?這是你精神的笑話。“而且,思考,我意識到她是對的。
- Volodya,在您看來,Masha從臉上拿走了一些東西?
弗拉基米爾:我想是的。但是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在我看來,有女人明智的心,它在一些犧牲中表達。馬什有這樣的品質,我認為她把他帶到了臉上。
阿格里帕納:雖然我們與Masha非常不同,但是當我看到的時候,看起來,它看起來像,她喜歡什麼,我明白它不是由我專門形成的,而是通過我的例子。我理解衣櫃,鋪設了幾堆的東西,表明這件衣服可以來瑪麗,這絕對不是。但她拿走了一切。我說:“它不會坐在你身上,因為我有第四十八尺寸,你有四十秒,”但她奇妙地讓我相反。當然,它看起來是免費的,也是非常和諧善良的。我絕對猜測我喜歡沃體。我們家人的所有成員選擇香水。我非常喜歡香水,完美地關注他們。

並在“不是” - 一個盲人墜入愛河的女人
照片:Agrippina Glass和Vladimir Bolshaya的個人檔案館
- Volodya,而你,在我看來,可以猜出面部的東西......
弗拉基米爾:一世?!不是。我知道她的商店。並且銷售婦女告訴我這個場景,例如,Merila是這種服裝,但她沒有足夠的錢。然後我買它。這簡化了任務。然後多年來,她有一個衣櫃。然而,Mashka是清潔的,但仍然難以取悅。似乎已經是一切,雖然很明顯,總有一個小女人。我們,男人,合理地接近問題:“如果你有皮草大衣,你為什麼需要一個?”。
阿格里帕納:是的,他說:“哦,多麼漂亮的連衣裙!格蘭卡,你真的去了,但你有它嗎?!“ (笑。)
- volodya,以及你現在想要看到臉的什麼風格或什麼樣的風格?
弗拉基米爾:裸體。 (笑。)
阿格里帕納:有趣,我甚至沒有期待。 (笑。)
- 現在很重要,你們每個人都是什麼樣的?
阿格里帕納:我認為這個男人看起來像是一個女人的臉。如果他是醜陋的話,它稍微穿著 - 這是她花園裡的一塊石頭。這對我與Volododa和Danili有關,也很重要,也是甚至爸爸。如果您對我附近的人看起來不像那樣,我會感到不舒服。
- 他們說,為了節省感情和家庭,你需要努力解決關係。你有沒有工作?
弗拉基米爾:我會稱之為不起作用,但只是能夠找到妥協。
阿格里帕納:家庭生活並不容易。雖然另一方面,你不需要“只是”的愛。不可或缺的情況是聽到伴侶和一些緣故。
- 但從來沒有一秒鐘沒有想到?
阿格里帕納:不是!
弗拉基米爾:雖然我們不在乎沒有衝突和糾紛。但有時即使你認為有必要放棄。我想我沒有說什麼新的。
- 以及我們通常發生的爭吵?
弗拉基米爾:一旦聯合創造力開始,排練,就會立即產生摩擦。一個領域的兩個非常明亮的個性,所以火花了。
阿格里帕納:在我看來,對於我們來說,應排除聯合創作過程。 (笑。),幸運的是,很少發生。雖然我們有時忙於一些表演,但我沒有接觸到那裡。當合作夥伴只存在於“所有藍色色調”中,很久以前 - 在“雅克和他的先生”中。這也是恐怖。

生活中的快樂夥伴,在阿格里帕納和弗拉基米爾的舞台上,不要感到非常舒服。 “所有的藍色色調”
照片:Agrippina Glass和Vladimir Bolshaya的個人檔案館
- 現場,但現在你在新的伏劇賽中玩耍。那麼為什麼?!
阿格里帕納:我玩了麻煩。 (笑。)
- 但這是她丈夫和董事的聯想決定發生的自願事項或一切恰好?
弗拉基米爾:當然沒有,不是鯨魚。然後發生了衝突,之後我們得出結論,通過聯合工作完成。但沒有什麼,你看到,坐在一起,沒有互相殺戮。表現出現,感謝上帝。
阿格里帕納:當她激勵他時,我們不是配對Olga Lomonosova和Pasha Safonova的選擇,他感覺像沒有董事。
- 來自那些像“男孩或鞭打的女孩”這樣的董事的Volodya?或者只是等待你的大成就嗎?
阿格里帕納:在我看來,一個親密的男人,是它的丈夫,妻子,兒子或女兒,父親或母親 - 總是“男孩毆打”。這是潛意識的。而且我還沒準備好成為極端。我想做創造力,雖然是不舒服的條件,但為了讓我責罵並鼓勵與其他人一樣。這是相等的。
弗拉基米爾:當外國人來臨時,當你作為董事必須組織它們時,你需要強大的後方和支持。首先必須了解你,你必須了解你,而且你必須花費少於別人的力量。當它發生不同時,它會導致刺激。
- Volodya,你是一個吝嗇你的表演的好話嗎?
弗拉基米爾:讚美,但沒有更多。
阿格里帕納:要客觀,我會說這個:不,他不是一個吝嗇,但不是很慷慨。 (笑。)我得到了,它在我看來,恭維等級,融合更多。有人刺激它,我沒有。
“Volododa,當我第一次看到臉時,你會記得那天的顏色嗎?”
弗拉基米爾:當然。她在劇院中展示,我在白痴中出發了。她去了舞台,演奏了杜松林,完美地發揮了。
阿格里帕納:所以他投票不帶我。
- 也就是說,一切都發生在現場。
弗拉基米爾:我們就像兩個機車一樣,互相曝光,發生了爆炸。
阿格里帕納:我也在舞台上看到了他。我被帶到劇院,他在羅密歐和朱麗葉梅特里奧排練。我去看看排練,他是厚顏無恥和灰狗的梅蒂奧。
- 也勇敢地征服你?
阿格里帕納:不,那我沒有贏。
弗拉基米爾:所以,開車。燒烤呈現。只是做了一個寬闊的手勢。
阿格里帕納:很快就有二十年的生活。和十年的婚禮。
- 你為什麼要那麼做?我覺得有些東西可以為這種關係添加一些東西?
阿格里帕納:我想是的。時機已到。我們的婚姻沒有註冊,暫時,我們沒有感受到這種必要性。然後他們決定,如果我以某種方式合法化我們的聯盟,那麼在上帝面前,而不是在國家之前。
- 之後,改變了什麼?
阿格里帕納:大概。我成了我的妻子,心理上改變了一些事情。以前,它仍然是一個女朋友,心愛。
弗拉基米爾:我也覺明,在別人結束之前,我也仍然是我最喜歡的女人的答案。
- 我記得之前,分手,你幾乎所有在時鐘電話上的費用。現在你也想念對方?
弗拉基米爾:是的,我想念。
阿格里帕納:一方面,彼此有強大的信心和總信任。它充滿了靈魂休息,並使一段時間平靜地讓它變得可能,沒有歇斯底里的存在。另一方面,我們已經習慣於彼此習慣,當我們分開 - 我們在溝通中感到強大的短缺。

瑪麗亞和丹尼拉 - 摘要兄弟姐妹,但彼此非常親密的人
照片:Agrippina Glass和Vladimir Bolshaya的個人檔案館
- 你能說你知道有關朋友的一切嗎?或留下一些秘密角?
弗拉基米爾:什麼樣的原始主義,你知道一切的人是誰?!
阿格里帕納:一些小區,靈魂的一個小顆粒,如果我們說可憐,必須關閉,只有你的。但我們並沒有完全了解自己。我怎樣才能說我研究了Volodya百分之百?然後,我們改變,發展,某事的年齡介紹。
- 你改變了什麼,什麼保持不變?
弗拉基米爾:場景是有才華的。因為有一個愛的女人,仍然存在。因為它是一個美麗,仍然存在。因為這是一個工作狂......有時它甚至是憐憫,我希望它停下來,在沙發上伸展並留下一點。但是最顯著的事情是她愛我。 (笑。)
阿格里帕納:就像Larisa在“Didnight”的關於Karandyshevyeva! (笑。)Volododa成熟和障礙,變得寬容。雖然有時我不這麼認為,但我會這樣做。在我看來,他性格的總變化也沒有發生。
- 你建了一個房子。誰以及參與的過程中的過程?
弗拉基米爾:在我看來,在公寓建設中,現在,在房子的設計中,我們劃分了責任。我有骯髒的工作:建設者,基礎,日誌。在最後階段,當窗戶,門,燈,壁紙,阿格里帕納的選擇已經進入。
- 你真的相信這個嗎?
弗拉基米爾:我們已經擁有修理公寓的經驗,所以我知道我的妻子有很好的品味。雖然窗簾我們選擇了兩個小時,但最後一個詞仍然留在臉後面。
阿格里帕納:我用Volododa建議。我有時很難做出決定,我不是專業人士。我們有一位朋友 - 一個裝飾者設計師,了解我們的口味,需要和覺得我們想在房子裡看到。現在他經常給出他明智的建議。但有時與他討論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很忙,在出發時, - 然後和誰一起諮詢?只有她的丈夫在這所房子里和我住在一起。
弗拉基米爾:在諾曼底,她一年前買了床罩,我甚至都不記得它是如何發生的。但她說:我會買 - 那是它。
阿格里帕納:我說沒有他,我會死。 (笑。我回答說:“是的。”我意識到我不能沒有他,因為它很好。現在它在家裡打了!

“房子很漂亮。但是展示次數需要去某個地方。這是一個在另一個空間中彼此相處的機會。“法國,聖米歇爾
照片:Agrippina Glass和Vladimir Bolshaya的個人檔案館
- 你的房子是什麼 - 一個悠閒地休息的地方,接受客人或其他東西?
弗拉基米爾:我們仍然沒有真正理解這一點,因為他們沒有住在那裡。
阿格里帕納:雖然我只想在那裡。房子很好,但畢竟你需要去印象。我從來沒有理解過,但我變成了,我理解我的父親,他們根本不休息。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真正的神秘。但是與新印象餵養的情緒餵食呢?在另一個空間中留在一起的可能性,在另一個維度,窗外的另一個景觀?這些不是空詞,我需要它。需要更新。
弗拉基米爾:當你問:“你們都相互了解嗎?” - 我以為我有一點秘密,我現在會揭示糧食。我在池塘里發射了池塘的白色阿穆爾品種。池塘開始吃得過多,這條魚吃了草。還買了三隻裝飾鴨子,他們現在在那裡游泳。
“在我看來,你需要Satirikon來致敬你的幸福。”
弗拉基米爾:仍然致敬?!所有關於(笑。)
阿格里帕納:我們經常給她。我認為一切:“和什麼?”。現在我明白了。
- 這位盛大一再說他可以稱自己是一個幸福的女人,而表情“幸福的人”原則上聽起來不那麼多......
弗拉基米爾: 為什麼?在我的協同臉上,有幾個時期的時候我真的宣布自己:“停止這一刻,你很好!”